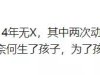每個一線城市,都有幾處日結工扎堆的地方,比如深圳的龍華市場,上海的車墩,北京的馬駒橋。

這裡散落著一群相似的面孔:他們多數來自農村,文化程度不高,技術能力有限,手停口停是他們的生活現實,前幾年,媒體的報導曾讓這一群體備受矚目。
而在中國廣袤的縣城和農村,同樣存在龐大的日結工群體。統計數據顯示,2020年,全國農村居民基礎養老金的平均水平是163元每月。
和城市的日結工相比,縣城和農村的日結工行業分散,機會相對較少,薪水微薄,從業者多數是60歲以上、沒有退休金或退休金極低的農村老年人。
不管出於何種原因進入這一行,他們的目標始終如一——掙錢。掙錢不光是為了吃口飽飯,也是為了不拖累兒女、不受制於人,在證明自己還有用的同時,也能排遣孤獨。
沒有退休金的農村老人,正在用最後的力氣換取晚年的體面。
干一天,活一天
前些日子,潤弟家每天賓客如雲,都是來「瞧」她的。
61歲的潤弟不小心踩空跌倒,把腿摔骨折了,女兒帶她去了太原市區最好的三甲醫院看病,醫生說需要打上石膏靜養6周,潤弟的活動範圍不得不縮小成臥室和院子。在農村,打石膏可是個大新聞,提著雞蛋牛奶來看她的鄉親們也多了許多。
這其中,不少是她的「鑔友」——華北農村辦紅事,習慣請鑼鼓隊助興,一台鑼鼓,兩邊配上十幾個黃銅大鑔,演奏時似雷聲滾動,大炮連轟,方圓一公里都知道你家有喜事。
潤弟從50歲開始幹這行,無論是指揮、鑼鼓,還是大鐃、小鈸,各個位置她都擅長。要不是腿骨折了,今年5月的婚禮旺季,她定會準時出現在市裡的各大酒店門口。「全市哪家飯店的茅房我沒尿過」,說起來也是她的光輝履歷。

這份工作不算太累,而且結錢快。早上接親出發前在男方家演一場,新娘子娶回來再敲打一通,到了酒店儀式開始,造個勢,等賓客進去吃飯,鑼鼓隊的十多個人就擠上麵包車回家。偶爾遇上闊綽的主家,還能吃口飯。以前30塊錢一場,現在35塊錢,演完當場就給工資。
「我這腿太誤事了,不知得耽擱多久。」眼看就快要錯過今年的婚禮旺季,潤弟懊惱不已。另一頭,她的小姑子二妮,則慶幸自己的腱鞘炎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,能重新殺回流動飯店洗碗。
農村辦紅白喜事,若沒錢去酒店,自己擺席又費勁,就會請流動飯店帶著桌椅板凳和服務人員上門。除了廚師是固定合作的,剩下的服務員,都是在附近村上現找的,幹些洗碗、擇菜、擺盤、傳菜的活兒,基本都是女性。
二妮在流動飯店洗碗多年,工資比潤弟高些,一天能掙一百塊,有時候還能附掙盒煙。不過這錢掙得辛苦,得一直埋頭苦幹,雙手不停地在全是洗潔精的油污水裡攪和、洗涮。冬天零下十幾度,沒有熱水,三層膠皮手套也難以抵擋洗碗水的冰冷刺骨。長年下來,二妮得了腱鞘炎和頸椎病,下蹲都困難,掙的錢全還給了醫院。
二妮身高不超過一米五,人長得又瘦又小,可是幹活很捨得出力。領事的「頭兒」見她為人實在,有活就叫她。
通常情況下,二妮一個月能出兩次活兒,趕上臘月事宴多,能出四五次。這三五百到一千的收入對她來說,就是全家人的日常開銷錢,一家人都指望著這錢過活。只要有人叫她,50多歲的二妮來者不拒,她說,她希望自己一直能幹到干不動為止。
去年,建築行業下發了超齡限制清退令,出於安全考慮,男性超過60歲,女性超過50歲,都不能再進入工地。這意味著老年農民工失去了最重要、最高薪的掙錢途徑,沒有退休金的他們,只能流入餐飲、家政、保全等零工領域繼續開卷。
「幹活,就是干一天活一天」,潤弟說。她最近腿腳剛靈便了,摩拳擦掌準備重新出道。往年的經驗告訴她,7、8月結婚的人也不少,她要趁機掙上千把塊,置辦一身好行頭,去參加小兒子9月的訂婚宴。
不是誰都能掙這份錢
在農村,能出門打零工的老人,都是被同齡人羨慕的對象,因為這至少說明你身體健康、年齡不太大、沒有疾病纏身的另一半、不用照顧孫輩。但凡有一個條件夠不上,都只能待在家裡等待兒女的接濟。
一直在市區幹活兒的韓大爺,去年因為年紀大被澡堂「勸退」了。他70多歲,身體越來越差,走一步搖三下,隨時可能哮喘發作。澡堂實在不敢要他,給他女兒打電話,讓她把韓大爺接走。
此前,韓大爺在澡堂工作了十多年,住在門口兩平方米的看門間,平常負責在客人走後檢查水電並鎖門,活兒不重,一個月能有六七百,是女兒托朋友走後門得來的機會。這幾年澡堂生意越來越差,老闆自身難保,才狠下心把韓大爺送走。
看門、當保全這類無需技術含量的活兒,在打零工的老年人中頗受歡迎。但也有年齡限制,如果年齡在60歲以上,應聘被拒的概率會很高。僱主的理由很實際,「你年紀那麼大,萬一遇到劫匪、強盜或者小偷,你追他,你猝死了,算誰的責任呢?」
長工不收,短工也沒戲。七八年前,潤弟家所在的村莊大改造,需要幾十個志願者站在各個工段口指揮交通,一天有160塊補助。剛滿60歲的老李想去應聘,沒聊兩句就被人家擺擺手打發走了。去年核酸檢測需求量最大的時候,村里招納了大批志願者,同樣有補貼,但只要體力好、能熟練使用手機的年輕人,很多老年人都錯失了機會。

住在城郊的俊梅倒是年輕,剛過50,人也麻利,可是照顧孫輩的責任困住了她。兩個兒子成家後,老大家生了三個孩子,老二家生了兩個孩子。兩個兒子都住在附近,俊梅整天忙成陀螺,即使這樣,兒媳婦還指責她一碗水端不平。
俊梅以前在附近不鏽鋼園區的菜地當過一段時間臨時工,一個月能拿1500元。沒多久,老大家的雙胞胎就出生了,俊梅不得不一邊照顧孩子,一邊照顧兒媳婦。好不容易雙胞胎大點兒了,老二家的娃又出生了。俊梅再沒了自我,奉獻所有的力氣給下一代和下下一代。不鏽鋼園區和麻將場上再也打撈不到她的身影,是啊,她哪還有閒工夫。
在鄉鎮級別的零工市場裡,超齡老人們只有在用工緊缺時才能被擴編收錄。
潤弟家鎮上的技校一直在招清潔工,食堂、樓道和辦公室的清潔工很快就招滿了,唯獨學生宿舍的廁所長期聘不到人。因為負責廁所的清潔工工資同樣微薄,但髒累程度卻是別處的幾倍,壯年婦女們不願干,只能由老年婦女來頂上。
最近兩年,鎮上引進了幾個工廠,需要聘請臨時工製作一次性水杯餐碗,一鐘點工資10塊。鎮上的年輕人普遍嫌工資太低了,不願意去,父母這輩再一次接過了棒。一開始工廠主還不願意要這些高齡日結工,但無奈訂單太多,生產跟不上,只能塞下他們。代價是沒有勞動合同,當天幹完就給錢,卻已經讓不少村民樂開了花。
老年零工市場的江湖
本就產業不多的農村,能帶來的就業機會更是寥寥。狼多肉少的情況下,為了掙錢,在靠著人情宗族維繫起來的鄉村地緣社會,隨處可見沒有硝煙的戰爭。

潤弟知道,腿折後,有那麼多人去探望她,除了她平常積攢的好人緣以外,還有更現實的原因。她自掏腰包買了兩個鑼鼓,花了800多元,鑼鼓隊的領隊正好用得到。平常潤弟出活兒,領隊不僅給她人工費,還給家什錢,潤弟一次能得130元,推都推不掉。多年相處下來,潤弟在領隊那裡也成了左膀右臂,每次缺人了,領隊總讓她幫忙找。
潤弟有了權力,心裡也打起了算盤。先安排親妹妹、弟媳婦兒和小姑子,再次才是好朋友、老鄰居和麻將搭子。誰和她關係好,誰就能掙上這30元,因此家裡高朋滿座,出門前呼後擁。小小的團體裡,潤弟享受著無上的待遇。有一回鑼鼓隊出活兒,休息間隙聚在一起閒聊,其中一人給大家錄抖音,唯獨落了潤弟,她心生嫌隙,以後出活兒再也沒叫人家。
私人小作坊如此,給公家幹活兒的門道更多。
在技校給人掃地的二蘭子,自上班後氣就沒順過。學校宿舍大樓里原本需要3個清潔工,之前只有兩人,相當於兩人掙三人份的工錢。自從二蘭子來了,其餘兩人的工錢縮水,自然不高興。
那兩人是鄰居,還都信奉天主教,每天說說笑笑一起收拾,有垃圾桶一起抬,掃地、墩地時相互幫忙。作為一個闖入者,職場裡的冷暴力時不時降臨到二蘭子身上,另外倆人幹啥都不帶她,想趕緊把她排擠走,可為了這一天55塊錢的工資,二蘭子忍辱負重,說什麼也不肯走。
令二蘭子沒想到的是,沒過多久,平日裡情同姐妹的倆人就因為利益不均鬧翻了。最近到了畢業季,一屆孩子們離校後,留下了不少生活、學習用品,兩人一邊打掃,一邊把好東西使勁兒往自己家裡帶,鍋碗瓢盆、嶄新的作業本、床單被褥、衣服鞋帽……只要能用的通通帶走。

為了搶奪這些物什,兩人也有了嫌隙:一人說明明她拿的盆兒是厚的,怎麼最後變成了薄的;另一人說暖水壺她原本提了四個,為啥一數少了一個;戰爭逐漸升級,最後,一人說上次打掃,另一個人拿走了學生的新鞋,要不是顧及情分,她差點就告訴主管了……有人在的地方,就有江湖,老年人的零工江湖裡,也避免不了你爭我搶、明爭暗鬥。
當然,也有人另闢蹊徑,自立門戶,不參與這些紛紛擾擾。
83歲的喬大爺,至今仍活躍在說媒的崗位上。他性格開朗,喜歡結交朋友,掌握著鄉里各個村單身男女的詳盡信息,只要有機會就給人家介紹。按照鄉俗,每說成一對兒,婚禮上不光能有證婚人的榮譽,男女雙方還會各奉上500元紅包和一雙新鞋,這筆錢,就是他和老伴兒的生活來源。
無處安放的晚年
每個到了知天命的年齡,卻依然堅守在零工市場的老年人,都有自己的無奈。
傳統觀念里,「兒女成家」意味著為人父母最大的任務已經完成,往後的日子能享福了。可若攤上不成器的孩子,勞碌的下半生才剛剛揭開序幕。
四毛年過五十又重歸職場,理由是獨生兒子生了兩個兒子,靠自己養不起,只能找父母來接濟。
四毛年輕時也是個闊人,吃穿用度都比同齡的70後哥們兒高一個檔次。90年代,四毛就開上了烏黑油亮的桑塔納,又因為只有一個兒子,負擔不重,別人白天黑夜地開大貨車跑運輸,四毛干一天,玩三天,是村里麻將館的常客。
然而,兒子東偉成家之後,這個家庭便開始走向拮据。東偉學歷不高,從小養尊處優,愛招惹是非,初中畢業就輟學了。一開始,四毛花了四十多萬給東偉包了輛計程車跑活兒,幹了幾個月,東偉便受不了了,天氣冷了熱了都不想去,每個月房貸、車貸都需要父親貼補,生了兩個孩子後更是天天找父母要錢。
為了維持整個大家庭的開銷,四毛的老婆去附近廠里做清潔工,四毛重新開始跑大車,都是不穩定的工作,可也別無他法。

也有些老人,經濟負擔不算太重,出去掙錢的理由主要是為了自尊,不願朝孩子開口要錢。
改花快70了,還每天進進出出地忙碌,自從老伴兒去世後,改花換了好多份零工,比如去附近的學校掃廁所、挖甜苣(一種中草藥)賣、撿塑料瓶廢紙片兒,鄰里鄉親從未見她閒過。
問及原因,改花說,「每天也沒啥事干,做點活兒還能鍛鍊身體。」
改花天性樂觀,想得很開,一天到晚樂呵呵的。幾年前,村里修路,給她賠了幾十萬拆遷款。改花家就一個兒子,老兩口手都沒摸過賠償款,就直接轉給兒媳婦了。後來村里建設美麗鄉村蓋小區,兒子一家搬上了樓,留父母在院裡生活。
老伴去世之後,兒子一家也沒說過把母親接上樓的話,改花拉不下臉主動開口,也不好意思總問孩子要錢,於是選擇自己負擔起晚年,用打零工維繫自尊。
她總覺得,如果財政大權還在自己手上,兒子兒媳就算為了討點零花錢,也會三五不時過來慰問。

改花做過的所有零工里,最辛苦的就是淘剩菜。她住的地方附近,有個批發市場,經常有菜販將爛菜丟在垃圾堆里。改花便一點一點挑揀出賣相還行的菜,拿去洗洗,再擺攤低價銷售,為此被市場管理人員趕過好幾次,還有人以為她是無家可歸的乞丐,好心施捨衣物給她。很難想像,她的兒子住著大房子,開著小轎車,而母親卻在垃圾堆里淘菜。
改花倒不怨。對她來說,這也是排遣孤獨的唯一方式。她不會用智慧型手機,老鄰居們也陸續搬走,加上孩子不常回家,身邊能說上話的人越來越少,做點零活兒,至少還能融入到社會的運轉中,打零工是她為自己找到的安放晚年的法子,畢竟,「不打工真就只剩等死了」,她自我安慰道。
好在,從今年開始,改花所在的村子,村委給60歲以上老人補發失地保險了,每人每月有700元,加上養老保險、退耕還林補貼,七七八八算下來每個月也能有1000元。
1000元,對大城市的年輕人來說不算什麼,但對於農村的老年人來說,卻能長舒一口氣,足以讓許多人安心地離開老年零工市場——至少吃飽穿暖,不用愁了。
改花說,她打算趁自己還能走得動,回老家看看,見一見多年未見的兄弟姐妹。忙忙碌碌過了一輩子,剩下的一點為數不多的時間,她想留給自己。